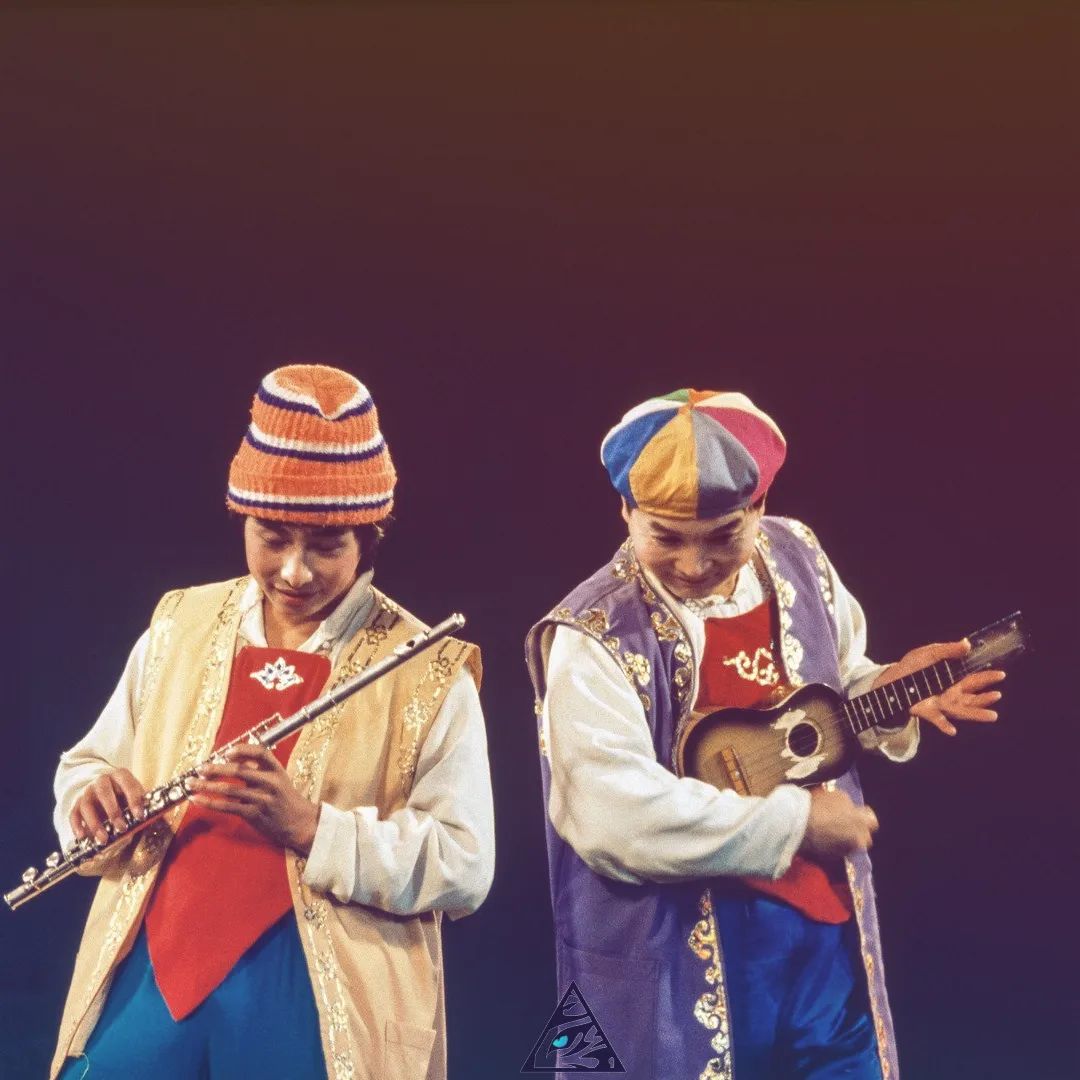去廣西出差那回,除了桂林、陽朔,因緣際會更跑到了柳州,地界邊陲的「程陽八寨」就坐落在柳州下轄的三江侗族自治縣,寨區顧名思義由八個侗族聚落組構而成;當天我下榻於此,晚來還與一群前來取材寫生的美術學院生、背包旅人等坐在小旅館裏談學論道,這是後話。
寨區內一所小學,正在大興土木、準備修築食堂,然而總體而言,本地教員的人數就和學生一樣寥落。值得一提的是,小學猶仍保有臺灣不少教改人士致力推廣的「無壓力學習環境」,反映在授課時間上,小朋友下午三四點光景便率先放學,中午亦得自由回家午膳、午休,蒙獲充分養息後再返課室,亦不嫌遲。
為了激發學習心志,學校大門邊的一堵灰牆上,周正寫著「讀書成就人生」,一枚枚光明磊落的紅字彷彿洋溢著朝氣。讀書成就人生嗎?我不確定,我真的不確定。
想起前陣子,不約而同和幾名友人聊到「博士就業」的問題,大環境的變化以及日趨嚴苛的求職條件已成定局,似毋須再贅言;然而我覺得最不堪的是,後設來看,這些年的發憤苦讀和勞力勞心,至此似乎淪為一種原地空轉的生命狀態──如同乾燒茶壺,如同行舟於陸,頭銜加身的新科博士或者根本就是《莊子》裏頭的朱泙漫當代版:「……學屠龍於支離益,殫千金之家,三年技成,而無所用其巧。」重點不在於所學工夫紮不紮實,重點在於「屠龍」之技難應用於當世,而學技者卻每每陷入無用武之地的我執,難以超拔。
由是,我才彷彿更加確信了:讀書改變命運,卻不見得能成就人生(這裏的「讀書」,實則更近於求學)。
也是才瀏覽的報導:三十四歲的印度億萬富豪尼克希爾.卡馬特(Nikhil Kamath)因為財富自由,所以得以有更多餘裕去思考生命議題。今年初,他在推特上發布自己研閱人類學家歐內斯特.貝克爾(Ernest Becker)專著《否定死亡》(The Denial of Death)的心得:「對我來說,這本著作可謂是年度之書了,如果以平均年齡七十歲來看,現年三十四歲的我,大概還剩下三十六年的壽命……人們總是很容易忽略生命如此短暫,如果你有機會在知道生命還剩下多少時間的前提下,重新再活一次,你會想做出哪些改變?」是啊,生命如此短暫,為什麼理想的人生規劃藍圖到頭來竟成了迷宮,困鎖多少表現優異卻輾轉徬徨的年輕生命?為什麼不設法忠於內在、盡其在我,卻千方百計要把自己安置於框框條條的目光間?
這樣一思索,益發替那些(曾經)篤信「讀書成就人生」的博士諸子感到惋惜。就像艱辛完成蛻變的蝴蝶,才剛破繭,就被頂上過重的學位頭銜給扼殺──無論如何,一切已經不能回到無垢的初生狀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