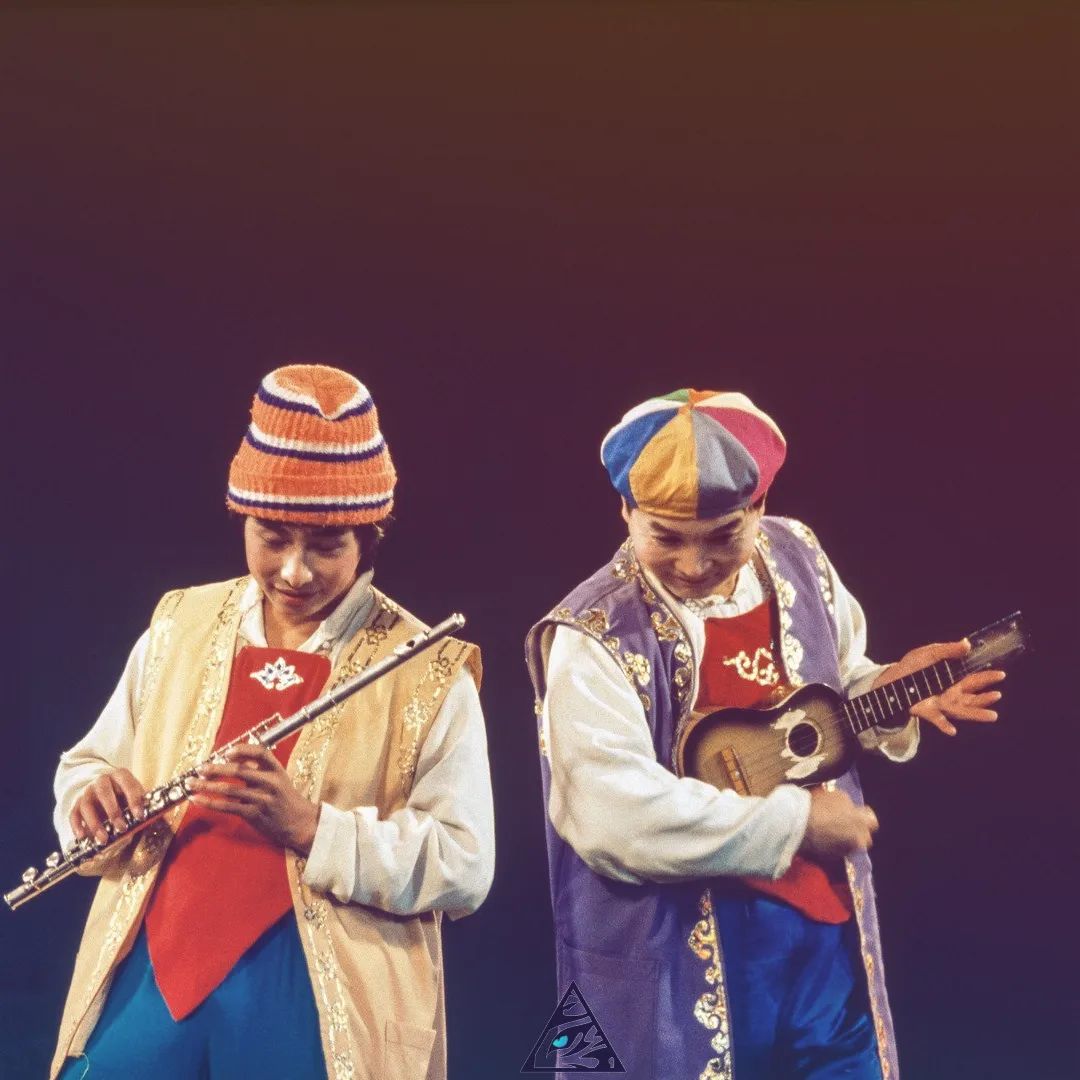剛寫完一篇文章,以孔夫子的話作為文章標題──於是忽然就想到,以前系上在籌辦年度表演時,某回曾經推出過一檔壓軸大戲:〈令人討厭的孔子的一生〉。
嗯,於我而言,孔子的確是令人討厭的……大概是中學時代遭受太多「文化基本教材」的荼毒,之後就算唸的是文學本科,除非「思想史」一類系定必修,否則我都盡量避免選讀任何帶有「儒家經典」的課程(比如四書)──我非常不願意進入四維八德的條框架構,不願意那些經世的道德教訓影響方寸靈臺,我就是很難用「後設」的研究角度把自己劃入界外──並且那個時候,我最迫切需要的,其實是來自風花雪月的養料,由是不免對性善/性惡之流的學說爭辯感到相當的厭煩。
後來因緣際會,在《禮記.檀弓》中發現一段記載:「孔子哭子路於中庭。有人吊者,而夫子拜之。既哭,進使者而問故。使者曰:『醢之矣。』遂命覆醢。」醢就是肉醬,活潑的子路後來因與蒯饋的家臣決鬥而命喪衛國,死後遭受醢刑(身軀被剁為肉醬);孔子命人「覆醢」,意思就是掩覆肉醬、從此以後撇棄不食用……睹物而思人,那細微的動作中蘊藉著一種深沉的悲傷以及對生命本身的感喟,剎那間我就感覺孔子依舊是個人,而不是「聖人」。
孔子在世時,實際上並沒能全然實踐自己的抱負,他想像中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,以及聖賢治國、詩禮傳家的社會,並不能見容於諸王野心勃勃的時代;他的晚年過得同樣不順遂,先是送走了兒子孔鯉,鐘愛的弟子顏淵、子路亦陸續離他而逝,降及魯哀公十四年春,君臣西狩而見麒麟現蹤,但座中竟無人識得此瑞獸,孔子由是洞燭了自己的命運:「吾道窮矣!」「莫知我夫!」……聖人出世,卻發現錯了時代,只得懷抱著不遇之志走向生命的終途。
這樣說來,還真的是「令人討厭的孔子的一生」。